1
我是皇长子,2017年2月13日,情人节前一天,我死了。
我还听得到周围的人慌乱,他们用力按压我的胸,试图复苏我的心脏;他们急急忙忙地打电话汇报这个消息,然后这个消息被带到了各国政要的耳中,这些政要当然包括,我那同父异母、势同水火的弟弟,当然,也许他一直在等这个消息。
我还不知道是谁杀了我,那两个把浸满剧毒药水的手帕丢在我脸上的女特工,已经坐着出租车逃远了,但我相信,她们不会被留下活口。
这世界上有许多位高权重的人想要我活;也有许多同样位高权重的人,想要我死。但我并不在意,因为他们的位置随时可以轮换,此刻想要我活的人,明天就会希望我永远地消失。
我死了,会有人难过吗?
我本来正要登上去澳门的航班,我的妻子在澳门,某些人说她只是我的妾侍,但这不重要,我要跟她一起过情人节。
我是一个在海外游学过10年,能讲铿锵高昂的母语,也会说流利的法语的人,据说,这分别是世界上最玄幻、最浪漫的两种语言。
我熟悉西方世界的节日,热爱他们的仪式感,但正是我的父君后来不再疼爱我的原因。
不管怎么说,我要去过节了,过一个我的父亲不喜欢我过的节。我的母国,我很久不能回去的母国,此时正在举办纪念我父君诞辰75周年的活动。也许他在天上正望着去赶飞机的我说“你个死性不改的浑小子”。
但他很快就可以当面骂我了,因为我这就去见他了。
2
这个世界的喧哗嘈杂正在离我远去,那些久远的往事渐渐清晰了起来。
1971年,我出生了。
我的母亲是一位本土影星。在遇到我父亲前,她有家、有丈夫、有一对可爱的儿女。
1968年,我的父亲,当时的太子看上了她。也有人说,他们疯狂地相爱了。父亲瞒着太子妃,和我母亲同居了,父亲又瞒着母亲,要求母亲的前夫离开她,滚远一点儿。
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年长六岁,有过婚史和一对儿女,这都让我的爷爷很看不上她,关于我的出生,爷爷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没有皇长孙的身份,不能融入皇族的家庭,但我也不能融入普通人的社交。于是,我的童年很孤独,我的世界里,只有那数的过来的几个人。
起初,父君很疼爱我,也很爱母妃。小小的我曾因为接受了牙医为我补牙,没有哭,父亲就送了我一部豪车作为奖励。我曾被抱进他的办公室,坐在他的御座上,然后他摇着我的手说“这就是你未来的座位”。
只是生在皇家,哪有什么恩爱绵长。我五岁那年,父亲又爱上了一位舞姬,母亲自此失宠,后来郁郁寡欢的她被送到莫斯科休养。
九岁那年,我被送去了瑞士,游学。我走那天,父亲抱着我,流下了眼泪,帝王的眼泪。
在瑞士,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“腐朽堕落的世界”。我在街上看到了许多,像我们家人一样胖的人,那里的每个人,都有机会像我父亲那样富足自由。

每年的生日,父君会给我打一个电话。通话时间并不长,但我知道,他爱我。
我十三岁那年,太子妃又为父亲生下了一个男孩,我的弟弟,今天的君上。
十年游学时光,我去了瑞士、日本、俄罗斯,我学电脑科学。这些国度的人并不知道我是谁,他们待我很好。但他们都鄙视我的母国,鄙视我家世代沿袭的皇权。
他们妖魔化着我的母国,就像我们在母国也妖魔化着他们。
3
1990年,十九岁那年,我回到了母国的首都。
十九岁的皇长子,游学归来,脑子里回荡的都是“男儿著眼天地间,万丈无涯是对象,一心志在开风气,不管别人怎样想”。
我见到了父君,他老了,又胖了。
我说“父君,我们也可以借鉴西方的某些制度,市场经济是能抓住耗子的猫,你看隔壁的那几个国家”,父君意味深长地看了我半晌,说“你先熟悉熟悉这边的情况,历练历练,我们再来讨论这些问题”。
有人说,我父亲是个封建君主,这样的评价对他有失公平。我们家的孩子,几乎都被送到“西方世界”接受教育,我父亲是个一直想有所改革的政治家,当然,只能以他可以接受的方式。
回国工作五年后,父君为我授予了大将军衔。他让我在尽可能多的工作岗位上历练,比如国家保卫部海外部门负责人、中央委员会宣传部指导员、公共安全部负责人、电脑委员会主席等等。那时,我是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,有政治势力选择向我靠近,比如我的姑父。

尽管在母国,也有许多漂亮姑娘的场子,可以夜夜泡吧。但我还是会想念曾经见过的那些摩登世界、灯火酒绿,工作不忙的时候,我会偷偷溜去日本的红灯区。
脱掉那板板整整的皇长子西装,我也是个喜欢买买买的大牌控。曾经有媒体拍到过我穿牛仔裤、白底黑条纹衬衣、头戴白色贝雷帽、休闲皮鞋的照片,后来有人认出皮鞋的牌子是菲拉格慕。

2001年,三十岁,我带着家人拿着假的多米尼加护照去了日本,在机场,我们被问讯了,护照被拆穿是假的,我的真实身份被认出。日本的海关公务员问我为什么来日本,我说想要带孩子去迪士尼。
迪士尼自然是没去成,这件事让我的父亲很不高兴。他不介意我们纨绔,但他介意我们没把纨绔的一面隐藏妥帖,他更没想到回国工作了这么多年的我,依然迷恋外面的花花世界,这让他感到不安。
我的父亲也许永远不能明白,我为什么沉迷于国外的花花世界。只要呼吸到红灯区那混杂的空气、看到那闪闪的灯光,我仿佛就又看到了自由的模样,所有人的自由模样。
2002年,母妃去世了,在莫斯科。我陪在她身边,却不知这荣宠一时,一生飘零,是我们母子共同的命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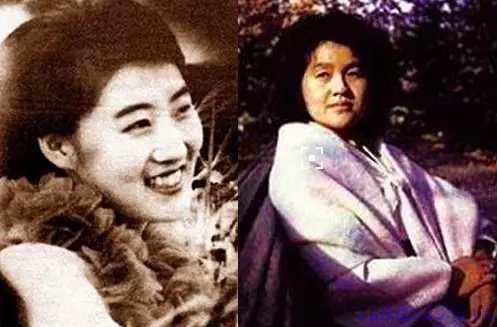
父君还在生我的气,为我的纨绔沉迷,我便开始在澳门生活,做一些国际贸易。姑父跟我说,以此做一些成绩,争取再次得到父君的欢心。
我的弟弟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脚,摩羯座的他更持重。在夺嫡之战中,他有着有利的筹码,他的母亲是夫君的正妃。

4
2007年,父君的身体日渐孱弱,姑父召我回母国工作。
2008年,父君中风,我奔去法国,带着脑外科医生来为他治疗,但这并未为我重新赢回他的欢心。他躺在病榻上,目光冷冷地扫过我,在他看来,这法国的医生与日本的迪士尼没什么差别,都是我对他的背叛。
于是我离开了故国,定居澳门。
生在皇家的我早就知道,我的敌人可以是我的兄弟,也可以是我的父亲。
我开始频繁接受记者的采访,谈论市场经济制度,谈论国内必要的改革,谈论政权不应世袭罔替。反正世袭罔替也轮不到我,我大可以谈点儿符合民主世界审美的话,做出一个温和坚定的改革家的模样。
毕竟,父君御驾未崩,姑父身体康健,一切都还有变数。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强国将我引为知己,我都有希望再与弟弟一搏。
我还偷偷地,在澳门开了一家赌场。首先,我喜欢。其次,我需要政治备用金。第三,我知道人们为了放纵,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。
2011年,父君去世,弟弟继位。我更努力地谈人民的福祉、告别封建政权的重要性。然而,弟弟的政治牌又稳又狠,并没有大国愿意冒险打破制衡的局势,扶我上位。
2013年,站稳脚跟的弟弟杀了姑父,我失去了最重要的一张牌。
大势已去,我还能做的,就是不断刷出存在感,在大国的庇护下,做一个政治备胎。
然而,失去了姑父后,连庇护我,他们都不是很上心了。
暗杀三番五次地向我袭来,而这一次,我没能躲过去。
我死了,在情人节的前一天。一千多年前,有一个胖子也在情人节前夜,被女人毒死了,那个胖子叫武大郎。但这不是同一个故事,因为那个胖子的弟弟替他报了仇。
我死了,在情人节的前一天,耳边仿佛又听见了那首歌,
“男儿著眼天地间,万丈无涯是对象,
一心志在开风气,不管别人怎样想。
人抬望眼大海高山,一息尚存亦向上
不必每日登峰顶,却也未曾改意向”。
但我不遗憾,毕竟,我看见过自由的模样。
作者 | 林默,微信公众号:花儿街参考(ID:zaraghost)
(本故事纯属虚构,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)

登录后发表你的伟大言论!
立即登录 注册